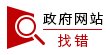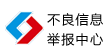■李德生 文
小满已过,说着说着芒种就到了。在这个季节,鲁北平原一片片黄澄澄的麦田,金穗随风摇荡,麦浪起伏,又是一年麦黄时。
抵不住新麦清香的诱惑,我推出骑了几十年的坐驾——自行车,走出家门,跨上车子,迎着初升的太阳,向田野而去。
不一会来到郊外的麦田,把自行车一放,走在田间的小路。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一片黄灿灿的麦子,麦穗颗粒饱满,沉甸甸的,麦杆坚挺,骄傲地昂着头,仿若在向劳作的主人展示它们的成果。
我爱金灿灿的麦田,喜爱这麦香味道。
初夏时节,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晨风带着几分凉意拂过脸面,格外清爽。时不时空气中飘来淡淡的氤氲麦香。阳光透过云的缝隙,温柔闲散地洒落在麦穗上,微风吹过,金黄色的麦穗被吹得左右摇摆,似大海中翻起的波涛,一浪推着一浪。这金黄的麦田,是流淌的河流,是欢腾的海浪,是守望者用心铺开的幸福梦想。
在麦地阡陌上漫步,不时还听到那抑扬顿挫的“布谷”声。布谷鸟的鸣叫,勾起我儿时的记忆。冥冥中,我总是感到,这阵阵“布谷”声,是为乡亲们丰收在望而发出的欢乐赞歌,叫人心生欢喜。
芒种到了,意味着北方已进入夏收。麦收是农村最忙碌的时节。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时间短,要保墒保种。没有在农村种过地的人,是无法体味又忙又种的辛苦。
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芒种时,天气多变,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可能暴雨倾盆。此时的麦子已经成熟,过高的温度会使麦穗炸开,造成落粒。而遇上暴风雨,可能会使麦子倒伏,给丰产收割造成麻烦。遇到阴雨天,麦子还会发霉发芽。一不留神,半年的收成就会受到极大损失。所以,一到麦收,生产队都要组织抢收抢种,颗粒归仓。
记得小时候,每逢麦收时学校都要放假,老师、学生都回家参加收麦。那个年代,没有机器,没有收割机,麦收靠的就是人们的双手。能拔的就用双手拔,不好拔的就用镰刀割。
麦收,从看着大人拔麦收割,到长大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才深知父辈们劳作的艰辛。俗话说:“农村三大累,拖坯打墙拔麦子”。 拔麦子可是个力气活,名列农村三大累活之一。
拔麦子看着简单,其实也有窍门:一要手有劲,二要会用力。下手抓麦时,手抓得不能太高,抓高了不仅用不上劲,而且还拔不出来。手要靠麦杆下面抓,抓死往腰后拉。因为拔麦子是墩着干活,拔一把就往左腰下夹一把,到夹不住了就用一小缕麦子打摇子捆起来。这个活,干一会就会腰酸腿疼,手胀胳膊麻。没有点劳动者的坚强和韧劲,是干不来的。多年来,乡亲们就是用这种原始方式把麦子收回来的。直到后来有了拖拉机、收割机才从劳苦中解脱出来。
农谚道:“芒种三日见麦茬。”大人们在麦地里忙着拔麦子、割麦子。我和小伙伴就在后面捡麦穗、拾麦子。不时,还用手搓几粒麦子放在嘴里,嚼一嚼,麦香悠悠,别有味道。
到收工时,有时还找一把尚青的麦穗带回家,放在灶火上烧烤。麦芒燎没了,麦穗烤熟了,我和姐姐就把麦穗放到小簸箕里,用手使劲地揉搓,把麦糠皮搓下来,簸掉,剩下的就是烧烤好的麦粒了。这香喷喷的大青麦粒就成了我们解馋的美食。放到嘴里一嚼,满嘴都是麦子的清香,这烧烤的麦子比生吃更有一番味道,越嚼越有味。
当忙过麦收,父母用新麦磨的面蒸出馍馍,一进门就会嗅到从馍馍中散发的麦子清香。
那清香,芬芳了我的整个少年时期,以至于后来,回荡在味蕾间的都不足以,与深藏在记忆里的麦香媲美。
那清香,无论我走到哪里,落脚何处,总在不经意间又被我嗅到,不经意间让我想起儿时的那一颗童心,装下不那么多烦愁,虽然生活清苦,时光总是快乐美好。
 沪公网安备31011002000548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3101100010
沪公网安备31011002000548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3101100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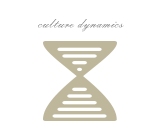 文化信息
文化信息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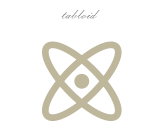 文化风采
文化风采 文化资源配送
文化资源配送 非遗文化
非遗文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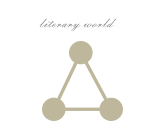 文苑
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