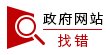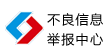本人从小就喜欢看电影,迷上了国产片,后来又喜欢上了译制片。译制片是经过译制配音加工的影片,那时就只知道是外国人讲中国话的电影,是外国电影,外国片。
我第一次看译制片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国际电影院看了部苏联电影《普通一兵》,影片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中,主人公马特洛索夫在战斗中用胸膛挡住了敌人碉堡的枪眼,英勇牺牲的故事,又使我想起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黄继光飞身上前堵住敌人枪眼的壮举来。后来我知道,这部《普通一兵》竟然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部译制片。当时是由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我第一次看译制片,就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部译制片,成了我观影记忆中的趣事。
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举办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电影展,我接连看了《攻克柏林》《最后阶段》《第三次打击》《华沙一条街》《多瑙河之波》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译制片,增添了对革命历史的了解,受到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和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思想教育。
“万花纷谢一时稀”,文革中一场劫难降临,一大批优秀国产片被打成毒草,外国片就更难逃厄运了。苏联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仍然可以在影院上映。《列宁在1918》中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台词成了我们当年在遇到困难时互相鼓励的经典语言。
“文革”末期,阿尔巴尼亚电影在影院上映,被精神极度饥渴的我们视为甘泉。当年在农场务农,有次回家,刚到家里,姐姐就递给我一张电影票,要我去看新上映的阿片《海岸风雷》,我看票上场次是晚上9时10分,儿童艺术剧场。尽管是时间很晚的场次,我毫不犹豫独自乘车从虹口赶往延安路上的“儿艺”。影片反映了二次大战中,意大利侵略阿尔巴尼亚时,老渔民一家人反抗法西斯侵略各自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结局。后来农场里也放映了此片。
那个年头,每到阿尔巴尼亚解放国庆,都有一二部阿片上映。《宁死不屈》描写了女学生米拉和女游击队员宁死不屈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片中有段情节:“革命者还玩吉他?”是米拉在一名男游击队员弹吉他时的发问,他们一起哼唱了“赶快上山吧,朋友们!我们在春天加入了游击队”的歌曲,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另一部《创伤》,反映了外科女医生维拉的工作生活剧情,给我们了解东欧人民的生活场景打开了窗户。里面的台词:“生活中有欢乐也有烦恼”,“和朴实的人在一起,能纯洁自己的灵魂”。这些台词十分精彩,至今仍记得。还有《广阔地平线》《第八个是铜像》《地下游击队》等等,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虽然不是什么经典名片,但看了后,感到十分新鲜,也丰富了精神生活。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同阿片并驾齐驱上映的还有朝鲜影片,占据了当时译制片的半边天。反映朝鲜农民生活的影片《鲜花盛开的村社》中,有段情节令人乐不可支,片中老人看上一位身体粗壮的姑娘,有心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儿子对其相貌很不满意,老人板着脸说:“胖,说明她健康,听说一年能挣600工分呢!漂亮的脸蛋能长大米吗?”这句台词成为人们看电影后说笑中的谈资,使有的胖姑娘也“躺”着中了“600工分”的“头衔”。
文革结束后,迎来百花争艳的春天。许多译制片源源不断在影院上映。最先出场的日本影片《追捕》深受人们喜爱。片中日本东京国际大都市,繁华街头的景象令人极为震撼!而“英雄落难,孤胆追凶,美女相助”等情节极其精彩,高仓健的“杜丘”,中野良子的“真由美”,成了当时男女青年的偶像。那年月里,《未来世界》《生死恋》《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佐罗》《尼罗河上的惨案》《虎口脱险》《大篷车》《叶塞尼亚》《罗马假日》《简爱》《人证》等等,各国影片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映过的译制片《流浪者》《牛虻》《王子复仇记》《蝴蝶梦》《百万英镑》《红与黑》《勇士的奇遇》《复活》《好兵帅克》《警察与小偷》《冰海沉船》等等重又亮相于银幕,让老影迷们重睹芳华,兴奋异常!
那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是我难以忘怀的。“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谁活着谁就看得见”“对你我都是最后一次。”这些动人的台词,令人回味无穷。瓦尔特率领的游击队员们同德国法西斯斗智斗勇,场面惊险紧张,惊心动魄。
看多了译制片,对幕后配音演员也逐渐知晓和熟悉起来,他们都是配音艺术家,为中国电影观众打开了一扇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他们中有长影的白景晟、车轩、向隽殊、张桂兰、张玉昆、孙敖等,上影的邱岳峰、赵慎之、苏秀、毕克、尚华、乔榛、刘广宁、丁建华、童自荣、李梓、曹雷等。他们配音的影片都能出色地再现名著和原作的风格特色,真是“言之有情,传之有神,品之有味,忆之有形”,富有极强的艺术魅力。不愧为配音艺术大师!
难忘的画面,定格的镜头,精妙的台词,当年追过的那些译制片成为一种幸福的回忆。
 沪公网安备31011002000548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3101100010
沪公网安备31011002000548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3101100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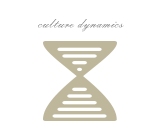 文化信息
文化信息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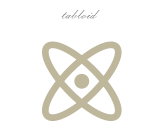 文化风采
文化风采 文化资源配送
文化资源配送 非遗文化
非遗文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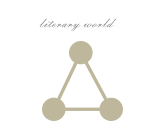 文苑
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