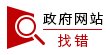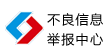“一夜腊寒随漏尽,十分春色破朝来。”
1978年8月的一天,我告别了“文革”期间在工厂的“战高温”劳动,带着组织部的介绍信到上海体育学院报到。党委宣传部于崇兴和茅鹤清两位部长接待了我,分配在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一开始就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帮助“文革”期间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整理发言稿。
体育,我是外行。马克思说过,欣赏音乐要有“音乐的耳朵”。那么,在体育学院工作,不是要有“体育的眼睛”么?于是,我抓紧学习、锻炼,看训练、比赛,同体育老师交朋友。见识多了,开始觉得“体育不简单”,感慨油然而生,又拿起笔,写了几篇短文寄给《体育报》(现《中国体育报》),都发表了。后来,报社还聘我为“特约评论员”。面对记者证,我更加勤奋了。
1979年的一天,院党委组织部部长刘华东同我谈话,要调我到复校后创办的《教学与科研》(内刊)当编辑。我不想去。第三次谈话,刘部长一改前两次叫“小戴”而称“戴炳炎同志”。我一听,顿时严肃起来,耳边回响起了在大学入党时“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誓言,立马表示:“我去!”又要与笔为伴了。
当期刊编辑,我是新手。改稿开始用铅笔,而陆明主任却让我直接用红笔,鼓励我大胆放手做。爱因斯坦说过:“人的最高本领是适应客观条件的能力。”我逐步改变了当教师的想法,投入编辑工作。首先向市高教局申请恢复《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取得“刊籍”,为期刊“正名”。名正方可言顺。章钜林院长兼任主编,结合审稿常同我谈学报工作,使我认识到“学报是高校的一个‘窗口’”。他卸任之际,还特地和陈安槐院长一起同我谈学报工作。那时,编印都是手工操作,我向印刷厂师傅学会了拆铅字,小修小改可以自己动手。“夙兴夜寐,一日无懈”,一心扑在工作上,想把“文革”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几乎将星期日、寒暑假都用上了,以致陆明老师要给我开加班“调休单”。
后来,学校先后创办了《竞技与健美》和《中国体育教练员》两本期刊,成立了期刊社,任命我为常务副社长、副总编(主编)。我没当过领导,又得学习。人少事多,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同仁们则“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勠力同心,相互支持,攻坚克难,摸着石头前进。如今,三份期刊都成为市高校精品期刊和特色科技期刊,《运动与健康科学(英文)》跻身“双学科库”世界前十。
到达退休年龄后,学校要我延长退休。怎么办?耳边响起了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的声音:“凡事要想得开,要往前看。”我服从学校需要,延长6年退休。2004年,辞海编辑委员会聘请我担任《大辞海·体育卷》副主编,并参与《辞海》第5版的修订。
编辑期刊之余,我还写了四百多篇小文章,有的还得了奖。参与编撰、出版了十余本书,为学校十多位老师出版的专著担任责任编辑,特别是首任院长《吴蕴瑞文集》的责编和注释工作。
人退休,笔未停。校庆60周年,我编纂了30余万字的纪念文集《绿瓦情怀》。至今还在编辑《绿瓦青松》小报。
我,一个出生于苏北农村的穷孩子,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是党一手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党给了我一支笔,我则“干一事,终一生”,努力像革命英烈萧楚女说的那样:“做人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高山仰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沪公网安备31011002000548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3101100010
沪公网安备31011002000548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3101100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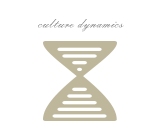 文化信息
文化信息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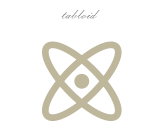 文化风采
文化风采 文化资源配送
文化资源配送 非遗文化
非遗文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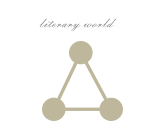 文苑
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