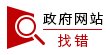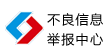■耿勇 文
上海不愧是万国建筑博览会,外滩那风格独特具有国际范的恢弘高楼大厦;如同繁星散落在城市“天空”的英式、法式等花园小洋房,无不向人们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厚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留沪工作第二年,便告别了白天办公桌上办公,晚上办公桌铺席就寝的日子。单位分给我一幢小洋楼中的一间房,我趾高气扬,颠颠地拖着行李入住小洋房。
小洋房位于江湾五角场,是战争的产物,日本侵略的见证。如果你乘公交车,从黄兴路快到五角场时,便能看到围墙内,一片绿树葱葱之中成片的花园洋房,因为门口有卫兵站岗,院内显得有些神秘,夜晚还有些阴森。
当初这里是空军政治学院。学院正门也叫1号门正对五角场,校名由徐向前元帅书写。入院后的三层楼,从上俯视呈飞机形状,故称飞机楼,是学院训、政、后三大部机关办公室,随后便是成片的花园洋房。据说,这里曾是日本人宪兵司令部。小洋房有几十幢,一律南北朝向,按现代话解释为双拼别墅。一幢两个门进出,住两户人家,且均为两层。每幢之间都是花园相隔,中间有小碎石路相连,户与户之间要走动也方便,曲径幽幽,漫步花间。不往来便有人高树墙,隔绿叶间隙相望。户户朝南是菜地花园,朝北是成片的水杉树。
早有鸟鸣,晚有蛙声。春夏时,花草之中蚂蚱蜻蜓等昆虫随处可见。晩上加班回来,昏暗的灯光下,伴随脚步声,总有嘭咚嘭咚的小青蛙在惊跳,草丛里也不时的发出窸窸之声,像是水蛇出洞,令人悚然,不敢靠近。
日式小洋房结构与英、法式相比,显得矮小许多,没有高高屋尖顶,小楼是木质结构,房顶上红色大瓦片,墙壁是灰色水泥,不过墙上水泥是不规则的,呈立体浪花式,突出处冒尖,这在当年抑或是一种风格。这类墙面壁虎很难爬行,因为一不小心会被刺伤划破。小洋楼的天花板、楼梯为木质,半个世纪,仍旧坚固,只是毕竟年久之故,虽木地板未变形,但楼上踏步,楼下心堵,因为嘎吱嘎吱有些响声在所难免。楼上两间一南一北,楼梯中间转弯处有个卫生间,楼下朝北是厨房,朝南那间与楼上一样。
那时房源紧,我们一个门弄住三户人家。楼上下朝南间12平方,面积较大,分别住有家有口且营职干部的两位干事,楼上朝北8平方我住,厨房卫生间为公用。当时我也知趣,一来是连职干部。二来是单身一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通常吃在食堂,不开伙。然后办公室加班写稿,很晚回来轻手轻脚上楼睡觉。那时大家挺默契,洗漱如厕的时间尽量错开,但不是一家人,却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总有些别扭。楼下孙干事娶个上海的漂亮媳妇,白净高挑。有好几次我去洗漱,她正巧在洗衣服,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害羞,她立刻避让窜回房间,咚的一声把门关上,很是尴尬。以致许多年后,即便大家都早已熟悉,偶尔相遇,还是有些不自然,因为当初同住一幢小洋房的别扭,产生不该尴尬的尴尬,总让人难以释怀。
组织上分配给我这间房,还装了一部内部可打外线的电话。领导反复告诫我,因为我是新闻干事,享受特殊待遇,否则连职干部,是不能住单间的。我一时受宠若惊,更加不分白天黑夜的写稿。
不过说心里话,享受了这个待遇,对我写稿的帮助远没有对我谈恋爱起的作用大。那时我找了一位自己中意的上海姑娘,我们谈对象,不必非到外滩爱情墙或者在马路上数电线杆,而是有了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她和她的闺蜜到我处来玩,一看进大门有士兵站岗,大院洋房花园成片,加上我有独立一间住房和电话,这在当时还是比较稀罕的。所以从谈恋爱到结婚异常顺利,小洋楼功不可没。
后来,学院新盖的楼房增多,住房有所缓解和改善。我也晋升为正营,终于享受独套待遇,楼上楼下,楼前楼后都归我一家居住,我也学着跟别的人家一样,把一楼朝南的窗子打掉,变成一个大的铝合金拉门,顶上装上大大的雨棚。出门有花坛,有菜园,再往前还有块空地,也学着别人家,搭起葡萄架,移种上葡萄。妻子爱美种花,花坛里月季花白天争艳,入夜,夜来香随风摇曳潜室润肺。我讲实惠种菜,一年四季,绝大部分时间都能吃上新鲜蔬菜,吃不了还送沪上的亲戚。
不过生态环境好,老鼠蚂蚁蚊子鼻涕虫等也少不了。它们都是“常住户”、“钉子户”,因为小楼地洼湿潮,虫多人烦,早晨起来,总能在水池边,下水道处看见几条黏糊,头上有两支“小天线”的鼻涕虫,怪恶心的。不过对付它方法很简单,在它身上撒把盐,过一会它就消失了。老鼠比较让人头疼,它通常藏在天花板上,有时一阵小碎步,咚咚快跑,有时谨小慎微,蹑手蹑脚踱着小步,后来我发现,它步伐的频率与我的动作大体相一致,我抬头望,它便停步不前,我拿起杆子做往上捅态,它便快跑溜之大吉。它居高临下从缝隙中能看见我,而我却看不见它。
当然这点烦恼,与享受大都市里村庄的生态环境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在楼上北屋临窗而坐,满目绿色,拂面空气清晰,如身置于深山老林。雨天靠在床上,聆听雨点打在屋檐上、树叶上、窗台上,才知道何为闲来听雨声。人长期“浸泡”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情高气爽,文思如涌。我怀疑前面那栋小楼里的张教授,著作等身,多半是依赖着一半学问,一半生态环境。
那时光,我们大家都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家庭小轿车,没有象征身份的名包名表,更没有钱周游列国。但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有小洋房,尽管它年代久远,有些陈旧,让人心满意足。
 沪公网安备31011002000548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3101100010
沪公网安备31011002000548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3101100010

 文化信息
文化信息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 文化风采
文化风采 文化资源配送
文化资源配送 非遗文化
非遗文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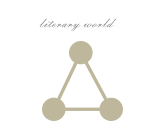 文苑
文苑